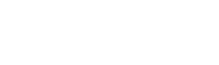父与子
儿子今年六岁,嘴巴长得小巧红润,眼睛圆大而有神,皮肤又白又净,这白净是从里到外犹若蛋清般通透的那种白,洁亮无暇,怎么看都惹人爱。这些先天的恩赐让儿子走到哪都招人喜欢,不管大人小孩都乐意逗逗儿子,抱抱儿子。作为父亲的我,显然是值得满足庆幸的。
孟子曰: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。儿子的出生,让我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。作为父亲,我之于这个家的意义就是顶梁柱。顶梁柱既要四平八稳,又得经受住风吹日晒,即便天开了一个窟窿,也要顶上去。
由于在陕北工作的原因,父子经常是聚少离多,这些年饱尝这方面的煎熬和等待,现在也逐渐习惯了,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陪伴儿子成为了一种难得的奢侈,所以儿子日常教育抚养都落在了妻子的肩上。鲁迅说:“看十来岁的孩子,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。”教育儿子,不仅要料想长大以后的事情,更要像浇灌培育小树苗一样,从小就要抓早抓小,日常下足绣花的功夫,合适的年龄做该做的事情。比如,从一些基础做起,自己穿衣服,每天刷牙洗脸,见人要问好,吃东西前要洗手,按时作业休息,这些习惯,是会让人受益一生的。有时,看着儿子调皮捣蛋的样子,看着他想上梁揭瓦的冲动,我便回想起小时候的自己,那不就是二十年前活脱脱的自己么,让人唏嘘。严管的同时,就会得到厚爱的回报,儿子一次不经意的问候,一次让人毫无准备的拥抱就觉得付出什么都是值得的。
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中,几千年来一直恪守并遵循着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的模式,在处理父与子的关系时,我既是儿子的父亲,也做他的知心人和好朋友,当然,这种关系更多是精神上的鼓励与共鸣,不是有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的说法么,多半如此。德国漫画家卜劳恩在其作品《父与子》中,将自己与儿子的生活经历用一个个生动幽默的小故事展现出来,诠释了不一样的父子之爱,那是西方父与子的幽默方式。生活中,儿子心细,记忆力好,这方面,他是主角,我是配角。比如,儿子教我怎样快速拼装一个玩具,教我怎样精准地在浩瀚如海的片库中找到喜欢看的片子,问一些啼笑皆非甚至匪夷所思的问题,小区外有几家超市,几家游乐园,几家儿童购物店,他喜欢的东西在哪个方位,哪个货架,哪一层上,他都心知肚明,每次,我都是被他拉着满世界地跑,我要做的就是扫码付钱。
陪伴可能是最好的教育。陪伴不是封嘴不说话,不是物质上的尽可能满足,不是说几句煽情的话,更不是敷衍了事,而是父与子共同去面对一些大事、挑战和困难,双向进入,相互走进,达到感情的融洽。去年国庆,儿子因为一次急性耳疾做了一个很小的手术。手术还没开始,妻子就在手术室外心疼地啜泣了起来,由于手术只能让一个人进来陪伴,我就抱着儿子上了手术台,尽管打了局部的麻药,但儿子疼得直哭,直叫喊,按都按不住,嘴里喊着爸爸,爸爸救我,后来,又开始喊,妈妈,妈妈救我,明显地感觉到那手术刀是在我的心口上一刀刀地划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,强忍着泪水没有掉下来,急忙催促医生快点。不到二十分钟的一个小手术,儿子哭喊地出了一身水,我也紧张地出了一身水。
当下,以武汉为中心的疫情席卷了全国,甚至蔓延到了全球很多国家,原本带儿子出去玩的计划也顺利泡汤,儿子到也安心,学会了主动戴口罩,外面回来后马上洗手,这是好习惯,好做法,即便疫情过去,希望他能保持这种好做法,是会受用终生的。
今年,儿子要上小学了,步入到他人生中的另一个学习成长的阶段,大考和磨练还在后面,希望他少点调皮和走神,多点专注和用心。(田宏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