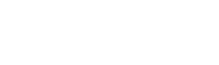【通世智库】袁延贤:和《国庆号》蒸汽机车相伴的岁月
2021-12-14 11:28栏目:资讯
七十岁那年,我陪老伴去北京做术后复查。儿子在北大参加同学会,到我住处,兴奋地说:“爸!你开的火车头在北京国家铁道博物馆里展出,要不要去看看。” “真的?那一定得去看。”我们坐上出租车,直奔博物馆。【作者:袁延贤;来源:通世智库;编撰:张小青】
买票走进博物,我一眼就看到我的“国庆号”2101蒸汽机车,它竟然和“毛泽东号”、“朱德号”并排站在一起,成了国家宝贵的文物。我直接朝着我的车快步走去。
一位男讲解员用讲解棒指着机车给我们说:“这台蒸汽机车是……”我摆摆手说:“不用讲,这我都知道,我就是这台车的火车司机”。“啊,我们可找到人了!”他扭头就不见了。
一会儿,他领着技术科的苟科长及七名男青年快步过来。他们每人手里拿着记录本和一支笔,苟科长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:“袁师傅,我们终于盼来了个内行,很多中外参观者提出不少问题,我们都解答不清楚。”
于是我接过讲解棒,围机车一周,解说了各大部件的名称、功能及整个机车的构造原理,并将苟科长拉上驾驶室,我坐在司机位上,讲解了汽门、调整阀、气压表、风表、大小闸、风动炉门……(展品车平时是不准游人上去参观的),他们听罢我的讲解,建议在大机件上贴个标注。我对苟科长说:“这样吧,我回去给你们印张图来。”并交待说:“这台车是无火回送来的,两个大摇杆卸下在水柜上,赶快找专业人员装上,不然车咋会动就说不通了。”最后我和老伴在车前照了相,还和苟科长合了影。

作者和夫人在《国庆号》机车前留影
“国庆号”蒸汽机车是由铁道部青岛四方机车厂生产。1950年8月,该厂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决议,要自产一台机车向国庆一周年献礼(解放前,全国四个机车厂都是维修车,不产车)。全厂职工日夜奋战,克服了种种困难,终于在国庆前夕,生产出我国第 一台蒸汽机车。
铁道部第一任部长滕代远请示国务院,正式命名“国庆号”,定型号为“解放I型”,编号2101。机车全长21.91米,总重150吨,牵引吨位2360吨,构造速度80公里/小时。四方机车厂还受命铸造了上嵌五颗星的“国庆号”大铜牌,镶嵌在锅炉左前方。另外还在锅炉上方安装了大铜钟,由绳索通到驾驶室,当牵引列车进站时,拉动绳索,使铜钟摇摆,发出悦耳的响声。当年威风凛凛、光彩照人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。这样的装置在全国国产机车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我原在河南省工业技术学校机械制造专业师范部毕业,后留校教物理和工程学,并兼任万能铣床试制组组长。

作者在授课
到铝厂后打听到开火车粮食定量高,司炉工56斤、副司机46斤、司机40斤,我便主动要求,且当上了司机培训班班长。经过短期理论培训便上了车,先从司炉工做起。
火车头的火室有半间屋子大,炉门又低,当火车闯坡大量用汽时,一弯腰几吨煤便进去了。火车司炉工的腰伤都是这么来的。我曾几次因腰痛从车上抬下。就这样我还是坚持下来,能节省粮票,补贴母亲。后来我升为副司机,主要负责油路润滑系统,也和司炉工替换烧火。原铁路局调来的老司机,多是解放前的司机,先后退休。三年后,我便率先晋升为司机。
我所在的中国郑州铝业公司,是国家于1956年在中原地区新建的特大型企业(简称郑州铝厂),还兼有一个大型水泥厂,直属冶金部。历时七年,先修铁路后建厂,铁路总长近100公里。黄河边还建有一个飞机场。领导讲话:“同志们,一吨铝一架喷气式战斗机!”
铝厂投产后,运量大增,上矿山的坡道太大(23%,就是一公里那头比这头高23米)。原有的杂型机车牵引矿石专列拉不上去。总厂向冶金部报告,提出调大型机车来,得到批准。
1966年秋,铝厂派两名火车司机去首都钢铁公司,接来了解放2101“国庆号”蒸汽机车,我有幸被分配到这台机车包乘组(三班九人),开始了和这台“国庆号”机车相伴十七年难以忘怀的生涯。
机车在投入运用前,我们首先将车上的大铜钟卸下,又将煤水车中不能用的推煤机拆除。我用大油画笔在铝板上写上“解放2101”字样,和同志们一起做成铝字,并在下边贴上木板使字体加厚,用黄铜管做框,做成红底、铝字、铜框的两块号牌,分别镶在驾驶室两边。并在火车头大灯正上方,用铜板模仿铜牌的繁体字,做成“國慶號”字牌,镶在做成的齿轮和两面红旗下方,用细纱布把大铜牌总是擦得锃亮。整个机车通体喷了黑漆,大动轮刷了红漆白边,看上去像新的一样,更加美观,现在中国铁道博物馆展出的机车上的号牌,仍然是我们做的原物。
“国庆号”机车在铝厂是主型机车。铝厂投产后,运量是产量的七倍,铁路运量也成倍增长。大运量的任务大都落在“国庆号”机车身上。我们企业的乘务员是12小时工作制:早七点至晚七点,晚七点至第二天早七点。
那时工资普遍很低。“文革”期间,铁路局出现个“36块5毛2战斗队”,这是二级工一个月的工资。国务院领导知道后,批准全国铁路系统6个工种:司机、副司机、司炉工、制动员、连接员、调车员,升一级工资,我们也跟着升了一级。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十年一次绝无仅有的升工资。工人是八级工资制,国家那年叫升才能升,且一次升职工总数的30%。领导很作难,为缓和矛盾,由升一级改为升半级,这样升级面积扩大为60%,升半级4-5元钱。
火热的夏天,人们坐在荫凉处光着膀子搧着扇子还嫌热,而蒸汽机乘务员却抱着一个15公斤压力的大锅炉,还得穿着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,脚上是特制的反毛牛皮鞋,一干就是十二小时,一天下来每人喝一大白铁壶水,十分辛苦。
下班前活多的很,需要特别认真小心的去做好。在水鹤处上煤上水,司炉清炉,将炉床摇薄,从炉门中用火钩将煤结的大火瘤子一块块掏出,副司机给摇连杆的油盅、压油机加满油,司机用检车锤对每个部位敲击检查,如有松动,用专用工具拧紧,还得将这么大的机车从上到下擦拭干净,等待交班。交接班需要半小时,手续十分严格,各种数据登记、技术指标和安全情况,清清楚楚。一天下来,累得坐在钢轨上站不起来,之后灰头土脸地到家拿上毛巾、肥皂、换的衣服去澡堂洗澡,等回到家吃上晚饭时,已是8点半左右。就这样撑一顿,饿一顿,机务员的胃病就是这样得来的。
上夜班更是难熬,尤其是夏天,我们住的都是简易房,房顶是牛毛毡红瓦,太阳一晒就透,屋内像蒸笼。我掂个凉席四处找地方休息,最后在玉米地里一个大柿树下睡着了,醒来爬了一身蚂蚁,休息不好,靠年轻硬撑着。解放前开车的师傅有句话:人非得弄到那没人心疼的地方磨炼才能 长本事。这话我记一辈子。
冬天调车作业时,机车不能调头,只能逆向推进运行。为看信号,扭头向后,半个身体伸出驾驶室外,任凭风吹雨打。冰雪丝打在脸上像刀子,身体半热半凉。调车员手提着信号灯,在冰冷湿滑运行着的车辆上跳上跳下,一脚蹬空,后果不堪设想。师傅曾说:“司机手里捏着调车员的命,不可有丝毫大意。”
一次,接到任务,将一列27辆水渣重车拉到水头车站。我向车站值班员抱怨说;“建厂以来,哪有拉这么多重车上山的,况且由米河站到水头站,这段铁路都是用解放前旧轨铺的,车不敢跑快,且是上坡。”值班员说:“是黄委会水泥厂的原料,修黄河大堤急用。大车(值班员对司机的尊称)就辛苦一趟吧,不计时间。”
当将27辆水渣车拉到水头站时,竟把水柜20多吨水烧干,煤也所剩无几。副司机、司炉工的整个工作服只剩下脚脖处一点干的,脸被火熏得通红,两人索性将工作服全脱掉,搭在蒸汽塔处烘烤,只穿三角裤头,汗流浃背地在站台上就着大白铁壶大口大口喝水。我的衣服也湿透了,敞开怀坐在站台石头上看着老百姓往水柜中挑水抬煤。一个当地老汉给我们三人一人一支烟,十分动情地说:“看来当工人也不易呀!”确实不容易,当时的口号是:“腿跑断、眼熬烂,大干苦干拼命干,少活十年也情愿……”苦不苦,比比长征两万五,累不累,想想革命老前辈”。吾辈何敢言累言苦!
铁路运输是由近20个工种联劳作业,如有一个工种出了差错,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事故。安全是重中之重,所以整天提心吊胆。
有件事使我至今刻骨铭心。一次我们拉矿车上山,本来在红石山站通过,突然看到道岔处值班员紧晃红旗,我采取非常制动停车,问:“啥事?”值班员哑着喉咙说:“山上溜车了!”他急忙把道岔搬至岔线。我立刻明白,二话没说,开着车进了岔线。
岔线河务局的人正在装车,我不停地大喊:“闪开!闪开!”,便开着车向片石车一辆一辆撞掛过去。当我拉的矿车尾部一辆刚过道岔,值班员急速搬至正线位,还未站起身来,山上溜下来的四辆重煤车以八九十公里高速从他身边呼啸而过,帽子被甩得很远。如果撞上,火车锅炉爆炸,我们这些人将尸骨无存。
我下车,坐在石头上,头上直冒冷汗,连吸三根烟,一句话不说。副司机站在我身旁骂道:“他奶奶!这哪里是干工作,简直是在玩命!”我瞪了他一眼,不再作声。这时装车的人似乎明白了为啥撞挤他们的车辆,也都倒吸一口冷气。
那些年代,苦也就罢了,精神压力更大,尤其是文化大革命,职工分两派,你批我斗,领导“靠边站,有的职工干脆不上班,去干“革命”了。缺岗缺员,规章制度被当成“四旧”来批,本来脆弱的铁路行车安全环境遭到空前的破坏,事故不少,上班提心吊胆。
文化大革命结束后,生产秩序逐渐恢复。总厂批准运输部单独成立安全技术科,我被任命为第一任安全科科长。我心有不舍地告别了与我相处17年的“国庆号”2101机车。
那时我们科是全厂唯一配有专用汽车和照相机的安全科。我家小平房的窗户成了报警器,半夜一有人敲窗户喊我,房前房后的人员只穿裤头赶来问:“哪里又出事了?”
安全是天大的事。因此我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,就起草了“郑州铝厂铁路运输技术管理规程—工业站站管细则”。对有关工种的岗位内容、安全操作程序、责任担当等都作了细致明确的规定,使之干有所依,判有所据,极大地改善了安全环境。还整理了建厂以来的事故档案,一本血的教科书。

作者在办公室工作照
我下车后,我的“国庆号”机车仍在继续使用。后来,为了统一车型、统一配件,便于维修,杂型机车相继报废和调出,没想到我的“国庆号”2101机车在1986年前后,竟不知哪一天被调走,没来及和机车留个影,遗憾终生。
我的师傅和同事,大都因工作精神高度紧张、劳累过度过早的去世了,绝大部分得的是一种病--偏瘫。我的腰伤和胃病也时常发作。57岁那年申办了退休。在家照看双目失明的母亲和患脑瘤、心脏病的老伴,同时照看孙女和外孙,等这些事忙完了已是七十岁的老人。
我的“国庆号”机车也早已退役。当两位老者时隔25年在国家级博物馆再次相遇,其激动的心情是无以言表的。我伴着它度过多少个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,它的炉膛里燃烧着我十七年的青春年华。
“国庆号”是对建国初期蒸汽机车乘务人员的最高荣誉,“国庆号”蒸汽机车将在世界众多参观者面前永放光芒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,不管火车技术如何先进,不管时代如何变迁,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国家是怎样艰难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,更不能忘记一代产业工人为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,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与心血。【作者:袁延贤;来源:通世智库;编撰:张小青】
作者:袁延贤,《国庆号》2101蒸汽机车司机。